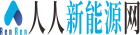我与女儿,我与地坛 每日动态
我与地坛
一本书的距离
【资料图】
我与地坛
一幅精神的图腾
我与地坛
隐秘一隅的咖啡馆
暑去秋来
来来往往
地坛还是地坛
“明天带我去星巴克吧!”
“去那里干嘛?”
我和女儿对咖啡都不感冒,喝完后昏昏沉沉尤为难受。
“我要去那里写作业!”
“家里不能写?”
“家里太吵了!”
怎么可能,楼上楼下不装修,小区也算安静,独立房间,何来吵闹。
她应该是想换个环境,厌烦了在一个地方写作业。
周边的两家星巴克,她又觉得不满意,想去个不一样的星巴克。
我不喜欢星巴克,不喜欢那里面的感觉,不喜欢里面的BUSSINESS,那就挑一个别样点的地方:地坛公园东侧的“我与地坛”。
01 ︳ 地坛再无史铁生
我与地坛,几百米的距离。
地坛与雍和宫自北二环南北隔河相望,一座逾500年,一座逾300年;一座是明清祭坛,一座香火不息为世代庇荫。
在杨万里的故乡,鉴湖公园盘的县城高中,我从语文课本里读到了《我与地坛》,16岁的年纪知道了一位叫史铁生的作家。
不知其故乡,想象不出他在地坛大树下静坐一天的情形,只是朦朦胧胧中知道了一种不屈的精神。
对于我们这些乡野出身的泥土学子,课本里的人物总是令人着迷,或许我们需要一种又一种精神的滋养,在王安石、欧阳修、杨万里、解缙一众庐陵文化先贤的故乡自豪里,对未来、对城市、对远方充满期待。
寡淡的岁月,闪亮的星光,一群少年孜孜以求,一代又一代走出乡村、踏入城市、走进象牙塔,与课本里的人物、地方无限地接近。
我与北京、我与地坛、我与史铁生会走得如此之近。
我的生活、女儿的学习与地坛仅一街之隔。
每每一到地坛,不由自主会想起史铁生,会下意识地寻找那棵大树,写《我与地坛》的大树。
多少次,奢望有不期而遇,驻足、仰望,找寻。
无功而返,一树似一树,或许它们都是他曾经的陪伴。
地坛已无史铁生。
一代又一代“我与地坛”,形式一个又一个。
比如这家“我与地坛”咖啡馆。
图1:三层小楼,浓浓的工业风
图2:老板是做进口汽车维修,浓浓公路风
图3:汽修老板想必是一个文艺青年
02 ︳ 精神与空间
曾多次跟女儿谈起“我与地坛”。
以至于后来,一提到《我与地坛》她就不耐烦:你说太多啦。
作为“10后”的她,一个在北京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她在以自己的方式构筑成长之塔,一种我不曾想象的样貌。
我老家是哪里?
我的故乡在哪里?
她很是疑惑,我亦回答不清。
我出生湖南,后随父母迁居江西,她出生河南,落户北京。
我的故乡在湖南,但我们一直回的是江西;生活在北京,但又找不出北京的归属。在这座城市,踩不到土地,踩不到落叶,闻不到泥草的清香。
哪里是她的故乡,哪里都是,但哪里都不是。
她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少年。
我暂时无法想象,没有故乡的人,将如何理解余光中的《乡愁》,或许是困惑,或许是更大的乡愁?
地坛于我,更像一副精神图腾。
地坛于女儿,仅是一座遗址公园。
一个精神象征,一个物理空间,无关对错,两个不同年纪的故事版本。
图4:二楼走廊
图5:浓浓的安藤忠雄清水混凝土式风格
03 ︳ 地坛与作业
刚放下午饭碗筷,装了四五本作业和一个笔袋,提着冬奥会手提布袋,一前一后出了门,带着她直奔目标之地。
“我们早点去,下午五个小时差不多写完”,这是她前一天规划的时间。
可能是中午的缘故,店里人不多,一二三层都有近半数的空桌椅。她在二楼挑了个靠角的位置,她要了杯热可,我一杯乌龙茶。
即刻开始了她的作业,我正在写这篇文章,也是在来的路上临时起意,用此来打发下午的”漫长“时光。
从小学五年级起,作业开始多了起来。
作业不需要我们管,不用过问、不用催促、只管在作业本上签字。放学写作业,吃晚饭,继续写作业,她的安排她自己知道,偶尔在她书桌上看到贴有零星的事项进度表。
她作业一本接一本,我在她对面显得无所事事,有那么个时间有些坐立不安,这文章里的照片就是在店里兜兜转转拍下来的。
她中途请教我两道地理题,我本以为找到了自我价值,竟然一道也不会,被她无情地”嘲笑“了一番:你连初一的题都不会。
帮扶、牵引、携手、放手、目送,我们何尝不是在与少年“渐行渐远”,某个瞬间会恍然,少年已长大。
大约三点左右,声音开始变得嘈杂起来,很多人来来回回根本找不着空座。
她专注如初,丝毫不受影响。
家里不比这安静?为何这种地方反倒成了她的专注之地?
有很多的也许,也许她也说不清的也许,那又怎样。
六点不到,她的作业全部写完,而我的这篇文章刚过半。
X 关闭
- 太阳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