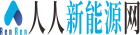生存实践的情感联系,为生活赋予仪式化,突出对美好愿景的追求 播报
《待绽蔷薇》的老妇人萨迪拥有摆满整个壁炉架的埃菲尔铁塔装饰品, 简一看到它们就被深深地吸引住。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简问萨迪,为什么她收藏了如此多的埃菲尔铁塔。萨迪回答说她热爱巴黎:她热爱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小皇宫……总而言之, 一切在旅游手册上被标记为\"推荐景点\"并附上一张永恒不朽的风景照的地方。
与那类活跃在各地风景中,将纪念品商店的物件当作猎物的旅游猎手不同, 萨迪是一个将在每周六玩一次宾果游戏视为仅有的娱乐活动的老妇人。
没有简的超市接送服务,她甚至难以闯荡茫茫的都市水泥丛林。在简描述自己的娱乐活动是和朋友携手游荡花世界并找乐子时, 萨迪无奈的叹气表明了她自己的闲暇生活有多么贫乏。
她问简,自己唯一的周末活动——每周六在圣安妮礼堂玩一次宾果游戏——这算不算所谓的找乐子。
萨迪还深深地为自己失去女儿的过去感到恐惧与无助 ,当她以为自己弄丢了简的吉娃娃狗小星星时,萨迪非常的沮丧、害怕和愤怒。
这种无助感令萨迪变为一个难以行动的人。她守着种满花的院子,像花朵一样扎根在居所中, 她甚至从来没有去过巴黎。
旅游城市是加大版本的主题乐园。作为旅游胜地的城市被幻觉的符号武装起来, 输出特定的体验给个体消费者,从而贩售商品。
这是后工业社会经济输出的主要样式。但它甚至不用发挥真正的旅游功用。不必由人亲身踏入其中, 与被精心构筑起的场景进行精密互动。
萨迪对简说,阿斯泰尔和赫本一起演了一部在巴黎街道上跳舞的电影(1957年的《甜姐儿》),她最爱这部电影, 也从而爱上了从未去过的巴黎。
简一看到包裹着巴黎铁塔的水晶球,就走向它,像个孩童一般伸出手,天真地摇晃它。“别碰这里的任何一样东西!”萨迪强硬地阻止了简。
与萨迪压抑了自己的行动能力,弃绝出门的这一行为形成对照, 水晶球的玩乐用途也遭到弃绝。摆设物的真正意义通过其无用性而凸显。
正如鲍德里亚所揭露的一种充满讽刺的真相:“消费物品的特点是一种功能的无用性(而这才正是我们所消费的)。\"。
再进一步,如果我们相信鲍德里亚对于电子台球背后隐藏着的冷漠的解说, 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现萨迪每周参加一次宾果游戏的日常之后藏着多么巨大的反讽。
在鲍德里亚的论述中,电动台球桌是伪装成实用设计的摆设物件的一项范例。这种游戏式活动只存有激情的表象, 实质上是光电、申动弹子和电子数值的符号的抽象操纵。
不断戳在数值卡上的印章,主持人广播与光电指示牌为这项参加者几乎全为大龄人士的游戏包装出一层充满秩序、紧凑、胜利者展露欢颜的假象。
真正的年轻人将参与其中,站着为一张张的宾果卡片盖戳。 这种出于自然活力的举动反而令萨迪感到尴尬。
当萨迪赢得宾果游戏, 周围所有人都慢条斯理地忙着自己手中的事,无人欢呼。
剥开由机器和主持人组织起的抽象操纵的外壳, 这个会场只不过在为一群老年人提供一个死气沉沉的合法赌博活动。
这场赌博活动每周六于圣安妮天主教堂的大厅内举办。不必对照周历表我们也知道,教堂与星期六的隔天, 即礼拜日之间的关系。
另一点不该被忘记的是,老妇人萨迪有一个生前酷爱赌博的丈夫, 他象征着萨迪的青春,但早早逝去。
在这之后,萨迪衰老,在每周固定的日子里前往教堂, 进行死气沉沉的赌博游戏。
在我们的文化感知中被许诺为多样而参差的都市生活,其实质在《待绽蔷薇》这部影片中被表达得尤为可疑。赌博游戏与教堂礼拜之间真的存在事实上的藩篱吗?
简对萨迪从未去过巴黎却有着大量的铁塔收藏品表示难以理解,因为简拥有年轻人的无限活力, 把亲身体验当做必不可少的享受生活的手段。
当她手中攥着一笔钱,与老夫人间的友谊甫一升温, 她就急不可耐地要带着萨迪去看看真正的巴黎。
值得注意的是,简也并不是通过游历巴黎的亲身体验迷上巴黎,而是被萨迪壁炉上的埃菲尔塔水晶球中的幻影所迷惑, 把飞向巴黎作为自己摆脱糟糕生活的梦想。
另一边,较为老派与保守的萨迪,则是每日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间, 借助全球化的物流网络获得巴黎的旅游纪念品。
如果我们愿意再深入探究下这些纪念品的来源,便会意识到, 它们当然没必要一定购自巴黎, 甚至连标签上的产出国、制造工厂所在地、销售地也不能清楚地标记出一样商品的血统。
资本以全球化的维度进行流动:制造工厂从全球的生产链条上的一处向另一处迁徙;\"制造业、服务业、行政事务(不断进行着)全球外包\"。
工厂、办公室和金融市场被解离为世界地图上零散的图块。讽刺的是, 旅游纪念品又极度受惠于旅游地点本身的附加价值。
它们向我们承诺,其珍贵性正来源于城市形象的独一无二。
就本质而言,简与萨迪对于体验生活的概念都被同一种拜物社会统治着。两人在享受生活的方式上的不同, 只是后工业社会中消费者心态的一体两面。
如果有什么足以令人惊叹的, 那就是可供购买的象征之物与凝附在其上的幻象的无处不在。
包围着现代社会的是“物的形式礼拜仪式”。 充满幻觉的消费网络完完全全地渗透进像是萨迪这样极为保守的老妇人的生活中。
像是《待绽蔷薇》这部影片所暗示的,旅游手册上的城市(以及在下文中将会提到的童年与主题乐园)是凝结成符号的美丽梦想。
它们通过虚幻的人造物指向种种美好幻景—一譬如黄金年代、乌托邦、休闲与快乐的体验、纪念意义。
在《橘色》与《弗罗里达乐园》中,它们还反衬了边缘者辛酸的生活或因冲击性的困境而纷乱的思绪。 边缘人对梦幻物的凝视展现了他们内心对美好愿景的追求。
《橘色》中的亚历珊德拉预订了整间酒吧作为圣诞前夜的演出场所。影片用极为温暖的笔调描绘了这场演出。
亚历珊德拉坐在红丝绒幕布前,镜头对准她, 像是凝视任何一名真正的歌星那样。
她在歌唱中深深地怀念童年时光:“栖居在小男孩与小女孩的玩具国,你感到无比快乐,一旦跨越童年的边境线,你就永远永远地失去了它。”,亚历珊德拉非常认真地对待登台演出。
她精心制作了邀请卡片,分发给自己的闺蜜和客户,包括出租车司机拉兹米克。她因化不出登台所需的隆重妆容而感到头疼, 对辛迪抱怨道自己不知如何是好。
亚历珊德拉还讨厌辛迪和黛娜在她的化妆间里吸食大麻, 因为这种低级的乐子在一次节日演出面前显得太不正式了。
作为节日仪式的共同维护者,她的朋友也尽力帮她维持演出现场的安宁气氛。辛迪和黛娜的争吵暂歇了, 一切都为圣诞前夜的演出做出让步。
节日气氛将要通过仪式进行表达。人们齐聚酒吧, 为了庆祝一个崇高的抽象概念。
在物资丰裕的条件下,仪式就经常以盛宴的形式表现出来。《橘色》中拉兹米克一家的亚美尼亚传统晚餐就是城市生活化的盛宴仪式。
对于辛迪、黛娜这样囊中羞涩的边缘人而言, 饮食的需求就要暂时放到一边, 先行完成亚历珊德拉的圣诞夜献唱仪式。
所以,当酒吧招待询问黛娜需要喝什么,辛迪抢过话头替黛娜发言:“她穷得叮当响,喝不起饮料,上一杯免费的水吧。”。
辛迪找到男友彻斯特之后,也对着他抱怨,自己兜里只剩两美元,一美元用来坐公交,一美元用来买甜甜圈充饥。 贝克对这种心态绝无批判的意图。
正相反,他认同仪式作为一种维系情感关系的手段的意义。
比如《橘色》中的酒吧,其功能当然不仅限于提供饮食。作为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的酒吧起着社交上的作用, 就如同古希腊的广场或十九世纪的咖啡馆那样。
当节日来临,酒吧就成为了一个经过选择的场所,以确保一次纪念活动(的举办)……在这里, 可能会发生相会或(关系上的)转型。
不仅现存的关系可以得到维系,新的关系和组合也可能起作用。辛迪与黛娜在演出后台暂时歇战, 两人间甚至滋生出惺惺相惜的微妙情感。
这正是人们在节日庆典时会流露出的特有的友好态度,有时, 庆典仪式对这种友好心态的要求也会带来相应的压力。
《橘色》中的亚美尼亚家庭用盛宴款待亲友,身为男主人的拉兹米克却试图找个借口溜出去, 与跨性别妓女辛迪和亚历珊德拉会面。
察觉到拉兹米克的心猿意马,一家人用言不由衷的闲谈和假笑伪饰着家庭内部的分崩离析。
同在节日晚会中缓慢培养友谊的辛迪与黛娜不同, 拉兹米克的家庭已经放弃了维护情感的可能性。
《弗罗里达乐园》里,稳定生活的轰然倒塌来得更加猛烈。女孩穆尼在汽车旅馆的生活中所积淀下的迷惘, 被即将与母亲分离的恐慌所点燃。
好友简希牵起穆尼的手,两人逃向她们一直向往的迪士尼乐园。这一幕可以解读为一个对未来保持希望及开放性的逗点, 同时也包含着深切的绝望感。
一个在边缘家庭中长大的女孩,以及与她同样出身的万千少女, 符合孩童天性地喜欢迪士尼乐园。 这种对美好愿景的追求能够在这样的世界中开花结果吗?
X 关闭
- 太阳能